欢迎您访问 米兰体育官方网站(MILAN SPORTS)精工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网站
全国咨询热线:
HASHKFK


 新闻资讯
新闻资讯 米兰体育
米兰体育米兰体育官方网站(MILAN SPORTS)赔率最高在线投注平台(访问: hash.cyou 领取999USDT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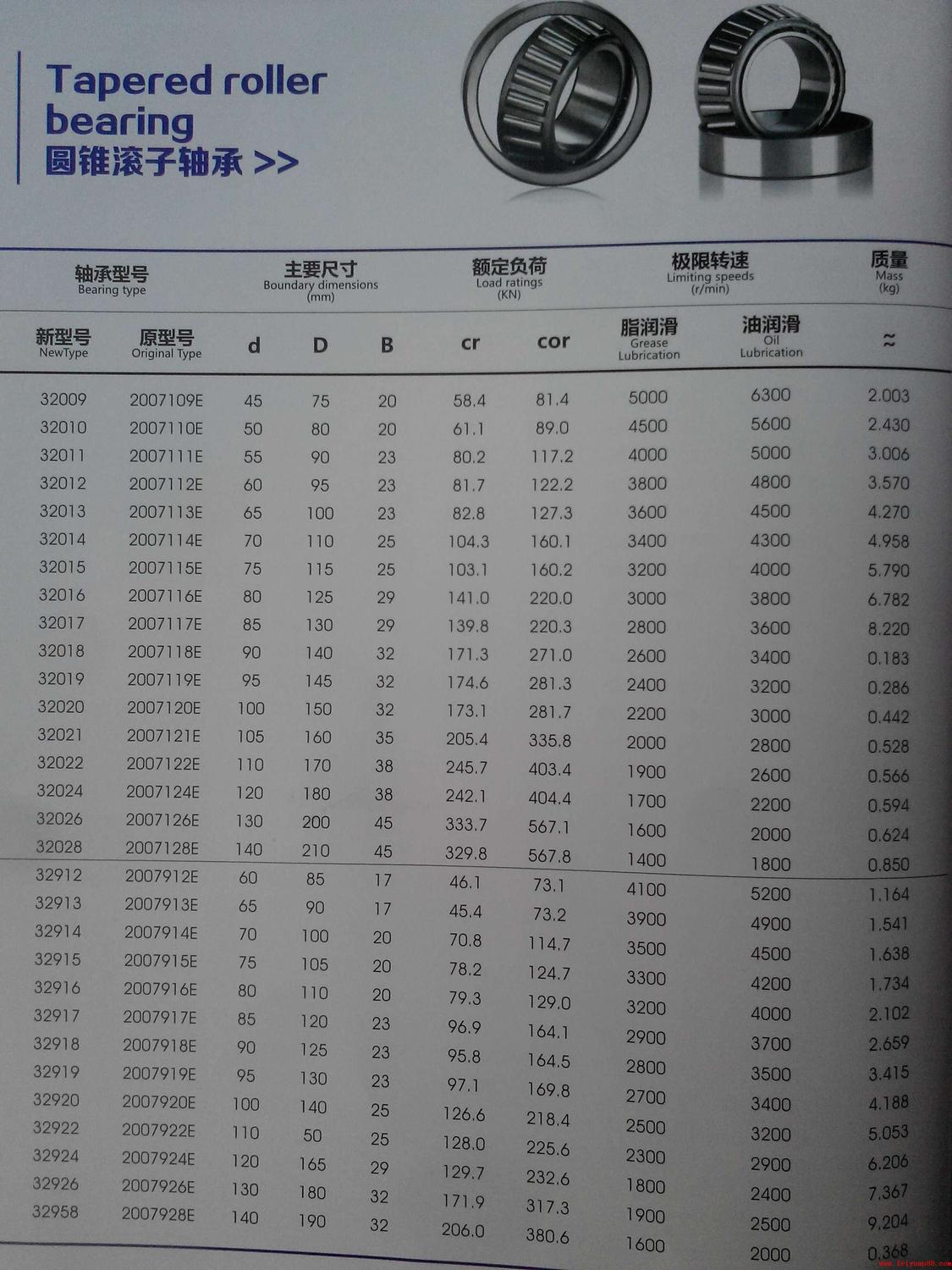
爷爷的太爷爷就是“開”字辈,算得上是我们这一脉的“祖宗”了。按家谱记载,他辈名“開裕”,“字祥雲,一字學廷,行杰二,清咸豐十一年(1861年)辛酉三月十五日巳時生,民國七年(1918年)戊午十月廿三日卯時歿”。陈祥云确实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。他考中了秀才!在那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里,竟然出了一个秀才!无怪乎爷爷会说“当时有十八台大轿来村里”。功名的获取让陈祥云在当地风光了好一阵,可很快他就因为与兄弟们不和而搬离高峰村。他选择在西边的茶山口村定居,带着他的妻子“易家张氏”和两个儿子——“纘”字辈的“纘集”(陈池十)和“纘式”(名字皆不存)。两村相距说远不远,说近也不近。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左右,但其间有孔目江相隔,又多有丘陵。当陈祥云跋山涉水来到茶山口时,由于他秀才的身份,茶山口村特地“聘了大轿,敲锣打鼓”去迎接他。一家人很快在这里落了籍。在不知不觉间,陈祥云一支已经开始脱离了高峰村的陈本占公一系。
所幸,西边不远的带源村中也有陈姓家族,亦即上文提及的带源村本初公系。虽然本占公与本初公世系不同,但两者同是行卓公后代。也许张氏当年的考量也正是此:寻求陈氏宗亲的帮助。至于她是否获得了实质性的帮助,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,长子陈文登的确出继给了当地“纘”字辈的陈江清,在此之前,江清一家只有两个女儿。张氏则又带着其余的子女,嫁给了当地的潘氏。到这里,爷爷这一支似乎要完全脱离高峰本占公系,转而加入带源的潘氏。也许是张氏改嫁时就与潘氏约定,又或者是当地陈氏的压力,陈美登、陈丰登并没有改从潘姓,而是保留本姓并在带源安居。至此,从高峰到茶山口再到带源,爷爷的太爷、爷爷的爷爷,爷爷的爸爸,三代人在三个村庄流转,高峰村的陈氏乡族是起点,带源村却远不是终点。爷爷这一支虽然脱离了“故土”,但是乡族似乎还在维系。这就是爷爷出生前的故事。
爷爷出生的地点是后来被分为带源大队下的五队新华村。不过这个时候,“新华”的名字还没有出现,此时它仍然归属于“带源”这个更大的村落集体。爷爷出生的屋子非常逼仄,是很典型的江西农村民居。两间木屋子紧挨着,屋后搭了一个草棚,有时养牛,有时养猪。屋子内几乎是家徒四壁,“撒吗都冒有,除哩两张榻”(方言音译,意为什么都没有,除了有两张床铺)。这是奶奶1969年嫁过来时看到的场景,在此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这一环境都没有改变。屋里屋外的地自然都是泥土地,不过屋里是夯实的泥土,屋外则是掺杂着鸡屎的松软黄泥。“鸡窝”是屋内为数不多的“摆设”,不过这个窝是“半地穴”式的,实际上只是一个浅坑,把木板一盖就隐去了它存在的痕迹。厨房、客厅、餐厅在农村里,这些都还是没有被发明的词语。“厨房”是露天的砖搭的灶台,两间屋外的一切地方都可以看作是客厅,餐厅则是流动的木凳。当时的贫穷可见一斑,而这只不过是带源村众多农民家庭的一户。
不考虑出继的大伯,按理说,爷爷应该还有一个伯伯陈美登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,陈美登随其母亲张氏迁到带源以后就早夭了,谱上只记载了一个“殤”字。爷爷的爸爸陈丰登一下子成了家里的独苗,爷爷也变成了“嫡长子”。等到了该上学的年纪,爷爷也很自然被家里送进了学堂。说是学堂,其实是村里的“栋梁”(即祠堂)改的,学堂的匾额上还写着“陈氏宗祠”四个字。整个学堂都是木制的,除了门口的匾和四角翘起的檐,外面看起来几乎和普通民居一样。学堂内部分上下两厅,上厅自然是老师讲课的地方,下厅则有几张用木板搭起来的桌子凳子,不过也常有学生从自己家带更好的木凳来。爷爷七岁上学时,恰好是村里选保长、打土豪、分田地的时候。爷爷家里土和田一共分了四亩左右。不过这时的爷爷并不关心这些,他关心的也许是放学后“剁完柴”和同学去哪里玩。
学堂里只有一个老师,姓何,是东北边白梅村的。他可能是爷爷当时能接触到的少有的来自“外村”的人了。学费5毛钱一个学期,课上教语文和算数。除了每天帮老师和家里剁柴,每天上课成了爷爷生活的重心,虽然略显单调,但是大体上安稳又快乐。那时的乡村也是平静的,虽然有点封闭,但村与村之间还依靠着血缘维持联系。“挂清明”就是这种维持联系的方式之一。爷爷的太爷爷陈祥云被葬在高峰村,爷爷的太奶奶张氏被葬在茶山口村,爷爷的爷爷陈池十也被葬在茶山口,所以每年清明节一家人就会一路东向,一路扫墓。从带源到茶山口再到高峰,“重走来时路”。当到了高峰,就和当地的陈氏宗亲一起去扫墓。这时扫墓就不分哪个墓是哪家人的“祖宗”、由哪家人来扫了,大家都搭把手,除草的除草、添土的添土,最后再一起放爆竹、烧纸钱。说是扫墓,对爷爷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春游。各种体力活自然是轮不上小孩的,他们只需要跟在大人身后,在泥泞又黏滑的山路上慢慢爬着。山路周围都是葛藤、松杉还有映山红等等各种枝蔓开来的植物。所谓“路”,也仅仅是一条由新踩扁的植物铺出的只能一人通行的小路。这种踏青的模式从爷爷童年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扫完墓以后有时还会在高峰的“陈氏宗祠”吃饭。高峰的祠堂相比于带源的要大上好几倍,是方圆十几个村子里最大的陈氏祠堂。扫完墓回来,几百号人乌泱泱地从祠堂四面的小门走进来,然后按关系亲疏远近、年龄长幼大小,选择七八人,围坐一桌。但是爷爷出继的大伯不在此列。陈文登彻底脱了高峰籍,融入了带源当地,就连现在族谱里也把他记在带源一支。他自然就是随着继父母在带源挂清明了。就像所有事物的瓦解一样,先在局部出现裂痕,再逐渐分崩离析。小的高峰村陈氏乡族在保持联系的同时成为那个出现破碎的局部,但是宏观意义上的乡族依然保持着隐隐的联结。
1956年,爷爷十三岁。他的读书生涯结束了。上学只要识得几个字,会算数,就够了。这是农村的共识。自此,爷爷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了看牛和种田等力所能及的农活上。大步一跃,短短两年间,整个农村的平静被激进与狂飙的热烈气氛所取代。新的“集体”出现,旧的“集体”被拆散、重组。“人民公社”、“生产大队”这些词突然产生,带源村从一个小乡村聚落,一下子上升到“带源生产大队”,统属于“观巢人民公社”。大队下又分了七个生产队,带源本村被“肢解”成“西头”、“老屋里”、“新华”、“连里”四个队,周边的“上山”、“生上”、“茶山口”三个村也被大队“吞并”成为另外三个生产队。大规模的整合确实一程度加强了村与村的联系,尤其是大锅饭吃“集体”——随便去哪个地方都有食堂吃。一时间“凡天下田,天下人同耕”、“有田同耕,有饭同食”天下一家的局面似乎形成了。但这种局面毕竟是短时间的,也是表象的。实际上乡村中原有的“姓氏平衡”被打破,新构建的集体并不牢固。
此前,带源村中有张、刘、潘、陈等主要姓氏。陈姓在带源地位相对弱势,但东边的茶山口村以陈姓为主,两村多少有点沾亲带故,真遇到困难邻村同姓也会帮一把,所以各村姓氏之间大体“均势”,“大姓”也少有机会欺压。随着生产队成为了新集体的基本单位,“姓氏格局”也被重新组织。西头张姓多,老屋里刘姓多,茶山口陈姓多……爷爷所在的新华村五队中则是张姓占了主导,二十多户中只有两三户是陈姓,姓氏“均势”的状态不再。加之生产队的独断性、封闭性——农活由生产队分配,工分由生产队计算,权力集中到生产队长个人,各种事项在生产队内部处理——“大姓”有了更多机会和借口来刁难。这些刁难又常常会伪饰成“队里的矛盾”,轮不到“外人”即其他生产队的陈姓来插手。如果矛盾闹大了,还可能被扣上不团结集体的帽子。新华村成了张姓的“天下”。在插秧放水、工分换算等种种小事上,“小姓”都受到刁难。其他“被张家欺负”的情况可能多如牛毛,可爷爷每次都只是半自嘲半洒脱地说,“在农村人少被人欺负还不正常吗?”
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1958,正如烧得红红火火的土炉子,当时的人们也处于一种狂热的状态。十五岁的爷爷加入了这场全民族的狂欢。挑土担石、剁树烧炭,爷爷的任务一下子加重了。所幸食堂还“蛮饱潲”(意为吃得饱),每八个人围坐一桌,饭不限量,菜通常只有蔬菜,肉偶尔才有。可这种日子也马上结束了……饥荒潜伏到村口,在秋收以后发动突袭。饿,是一种无法被填满的空洞感。挨饿的记忆在爷爷脑海中还很鲜明,一提到就滔滔不绝、滚滚而来。公社食堂“一斤米煮四、五斤。稀饭不像稀饭,干饭不像干饭。”1961年更是“吃了大苦”,“树皮、葛藤根、甜心菜(马齿苋)、山萝卜(党参),什么能吃吃什么”。有时候吃得好一点就是番薯煮饭、拌饭,又或者是糠磨成粉,做米饼吃。生产队的工作还是要照常做。爷爷一般是给队里挑牛粪、猪粪,挑到田里施肥,或者是去田里割草,草再堆起来沤肥。也有修水坝时帮忙挑土、装“土方”,挑一担土,给一片“乜嘚”(竹片)。“乜嘚”也分大小,爷爷这种非“劳动力”就只能拿小“乜嘚”,挣2、3工分一天。
一边挨饿一边干活总是难熬的。但饥饿又像时间的流逝一样,习以为常,以致于无法感知、无法言说。当饥饿感终于逐渐淡去,时间也终于恢复了秩序。农村的“三节”回来了。对于爷爷来说,端午、中秋、过年这三节意味着可以吃上肉了。生产队会特地杀猪,给每家每户分一点点。二两鱼肉、三两猪肉,这些都是难得的荤腥。虽然新“集体”的内部“大姓”与“小姓”的矛盾开始浮现,但生产队也实实在在作为一个共同生活的“集体”提供着温暖。除了“三节”发肉,年底工分算钱,生产队也承担着分发稻谷、菜籽油,晚上开会组织第二天生产任务等日常事项。何况要是收成好,工分还能多换点钱。在共同的利益下,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,“新华村五队”这个新造的“集体”被慢慢接纳。
也是在1962年,爷爷与高峰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。乡族受到了重创,却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恢复着。爷爷的妈妈温润英是皇华村人,温润英的妹妹嫁给了本村的一个木匠。靠着这层关系,爷爷向他的姨夫拜师学习木工手艺。一下子变成学徒的爷爷住在了他的师傅家,也就是皇华村。平时爷爷就跟着师傅去周边的村帮做木工。哪个村哪家人要打张桌子、凳子,又或者是甑子(蒸饭的炊具)、床之类的,就会请师傅去,管饭,按天算工钱,1、2块一天。皇华村不远就是高峰村,这也是爷爷和师傅重要木工生意的来源之一。按血缘算起来,高峰村里年长一点的都是爷爷叔叔伯伯、姑姑婶婶辈的。每年回去挂清明又都会碰个照面,一来二去就更加熟悉了。甚至修缮高峰的祠堂的时候,也请了爷爷他们帮忙。当学徒不到两年,除了高峰村,九龙口、江背、陂下、柳树塘……周边的村庄爷爷基本跑了一遍。
各个村从最初陌生的名字变成了村中一个个具体的人。就连学堂的何老师所在的白梅村,也从一个只存在想象中的“外村”,变成了“在这个村里吃过几天饭”的可知可感的“乡村”。在无意识中,一个具体又鲜明的“乡村网络”被爷爷所构建起来。“我们带源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,在山沟沟里。往西翻座山就到了上山河和西头,再往西就是双林。往南就是九龙口、老棚里,再走一点就到了欧里镇上……”以带源村为中心,每个村的地理位置得到了清晰的呈现。村与村之间就像驿站,一个又一个连接着,勾连起一张地图。相比于生产队,更原始的村倒变成了一个更鲜活的“观念”。生产队强行分割了村,可村的观念、村的认同还顽强地延续着。多个“集体”在此时并存,高峰陈氏乡族、带源生产大队、新华村五队,以及隐隐约约的各个村落所构成的一个更大的乡村集体。不过这些都只是模糊的概念,只有当爷爷离开了新华村五队、离开了带源生产大队,切断了与高峰陈氏乡族,切断了与乡村集体的联系,才能更清晰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。
3547部队电话员成了爷爷的新身份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、六点拉练跑操,白天训练七个小时接线架线,晚上有时候也要摸黑站岗。两个人一个铺,几十个人一个宿舍。从1966年到1969年,爷爷没有回过一次家。“思乡”的情绪从最初的饱涨到消弭。师、旅、团、营、连、排、班,每一个等级都可以视为一个集体,给离乡的人带来归属感。战争似乎迫在眉睫,恐惧与兴奋杂糅,更加强了对集体的依赖。尽管义务兵三年,爷爷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,但他确确实实和抗美援越擦肩。“当时连里面派部队援助越南,派炮兵连去。高炮三师也去了,就回来一个买菜的上士,保了一面军旗。”“第一批去的基本死了。”“我们团里因为搞演习的时候死了七八人,所以没去成。”“到六八年的时候,我们团里也派了人去,打了个转身就回来了,也没去几个人。”跳跃又模糊的叙事中,仍然能窥见“劫后余生”的庆幸。
班是兵营中最密切的集体。“当时成立革委会,实行军管。我们五班几个人是电话兵,跟着首长去开会。嘉兴、绍兴、杭州,浙江都跑膏了(意为跑了个遍)。”“每个月6块生活津贴,买点牙膏、肥皂。有时候还有战友偷偷买烟。”爷爷这个从十八线农村来的土小子,在各个城市间辗转,与班里的战友一同吃穿住行。国外的战争虽然无缘,但是国内的“革命”也轰轰烈烈。那段岁月似乎成为了爷爷生命中的高光时刻。乡族的羁绊被五湖四海的方言冲淡。“早上跑操,有七八种口音,喊‘一二一,一二一’。答‘到’的时候也是,大家普通话都不会讲。”爷爷的班里有一个江西宜春的老乡,其他人多是安徽、江苏和浙江的。“我们班长是长沙的,一开始班里都听不懂他说什么。除了江西的,其他人一开始反正也都听不懂。”各种口音在日积月累的磨合中,大家也慢慢熟悉了起来。一口蹩脚的普通话,时不时夹带着方言成为了交流的日常。“我也是那个时候学会抽烟,有时候训练太累了,不抽不行。还要偷偷躲着抽。宿舍里几十个人,大家都抽。训练好班长还会偷偷发支烟。”聊到这,爷爷又从口袋里掏出支烟点上。没抽几口,他就一股子把肺里的烟气全呼了出来,慢慢说着,“现在的烟还是没有当时的好抽啊。”
来回的通勤割裂着知觉,也割裂了工与农,城与乡。无论是宜春的轴承厂还是新钢的焦化车间,都只是形式意义上的集体。只有回到乡下、回到村里、回到家,才算是回到了提供温暖的集体。从冰冷的钢厂步入乡土社会,才是爷爷所熟知的那片土地。但伴随着经济滚轮飞速旋转,这片土地也快要变得面目全非。各村人开始一个一个外出打工,欧里镇上开始采矿挖煤。滚滚尘土中,一条条水泥路蔓延开。在时代的挤压下,各个集体逐一瓦解。乡族的联系因村里人员流失而渐渐淡化。清明节不再回高峰村,一方面是没有时间,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父母的逝去,二人都被葬在带源附近,扫墓也就在当地从简进行。陈氏乡族之间日益疏远。带源的宗祠如同它的木料,逐渐腐朽,无人问津。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存放村里老了的人的棺材。从学堂到灵堂,从儿时到暮年,它也被时代淘汰了。